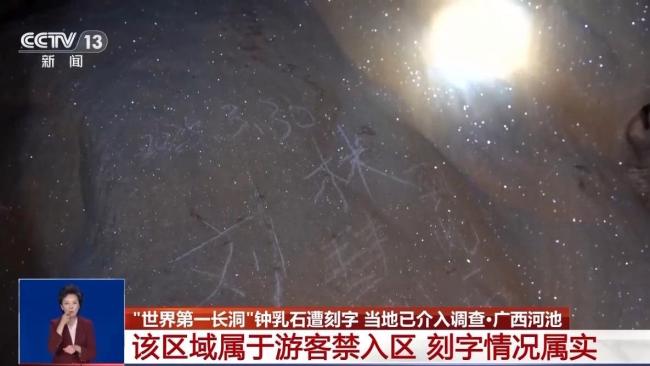《黄雀》编剧:不会美化罪犯 剧情漏洞频出遭诟病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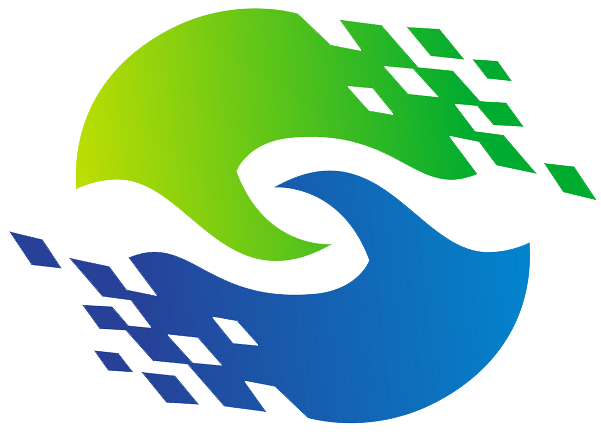 摘要:
《黄雀》编剧:不会美化罪犯 剧情漏洞频出遭诟病!昨晚《黄雀》大结局播出后,社交平台一片哗然。这部号称“反扒刑侦天花板”的剧集,从开播时的口碑炸裂到如今的槽点密集,完美演绎了“高开低...
摘要:
《黄雀》编剧:不会美化罪犯 剧情漏洞频出遭诟病!昨晚《黄雀》大结局播出后,社交平台一片哗然。这部号称“反扒刑侦天花板”的剧集,从开播时的口碑炸裂到如今的槽点密集,完美演绎了“高开低... 《黄雀》编剧:不会美化罪犯 剧情漏洞频出遭诟病!昨晚《黄雀》大结局播出后,社交平台一片哗然。这部号称“反扒刑侦天花板”的剧集,从开播时的口碑炸裂到如今的槽点密集,完美演绎了“高开低走”的烂尾模板。李红旗牺牲、佛爷落网、方慧反转成BOSS的结局看似热闹,实则漏洞百出:反派动机牵强如儿戏,主角光环碾压智商,多线叙事沦为故弄玄虚。
编剧试图用“原生家庭创伤”为全员犯罪洗白的操作,彻底暴露了创作上的投机与懒惰。当一部刑侦剧让观众只想问“这合理吗”,它的崩盘早已注定。
佛爷策划的“奖杯大劫案”,堪称年度最荒谬犯罪现场。为了偷一个体育赛事的奖杯,佛爷团队又是策反内鬼、又是献祭小弟,甚至全员上演“警车漂移”大戏。然而,奖杯既非古董也非天价藏品,唯一价值竟是编剧口中“佛爷不想错过的荣誉”。试问:一个靠偷窃发家的黑老大,冒着团灭风险抢个镀金奖杯图什么?这种强行制造冲突的套路,连抖音小短剧编剧看了都得摇头。
更离谱的是全员“甩锅社会”的设定。阿兰偷遍全城是因为被渣男骗过,财神走上歧途竟源于学生时代被诬陷偷钢笔。编剧仿佛在按头教育观众:看!他们犯罪都是被逼的!但现实中的反扒民警听了只想冷笑——哪个受害者的钱包里装的不是血汗钱?哪个被偷救命钱的老百姓活该当反派的情绪垃圾桶?
黎小莲的“高智商犯罪”人设,从第一集就开始崩塌。每次行动都靠“制造混乱→趁乱下手”的单一套路,连小区保安都能识破的伎俩,剧中警察却次次慢半拍。到了大结局,她更是化身“医学奇迹”:一针放倒佛爷的桥段,比《甄嬛传》的麝香膏药还玄幻。而李红旗的牺牲更让人憋屈——抓个小贼被捅成筛子,这是刑侦队长还是新手NPC?
反派的智商同样忽高忽低。佛爷前脚刚用“现金钓鱼计”把四眼骗进局,后脚就被黎小莲轻松反杀,精妙布局像个临时起意的玩笑。至于方慧的“幕后真凶”反转,看似惊天阴谋,实则全靠最后5分钟硬塞设定:一个美容院老板突然变成器官贩卖头目,铺垫还不如微商朋友圈的广告有说服力。
导演显然沉迷于“炫技式叙事”。每集开篇必插回忆杀,大春小春的兄弟情、花姐的养女线、金角银角兄弟的江湖恩怨……这些支线像极了短视频平台的“剧情解说”合集,看似信息量大,实则对主线毫无推动。直到结局才恍然大悟:原来这是给第二季挖的坑!但观众早已被灌了40集的“注水猪肉”,谁还关心续集菜单上有什么馊饭?
多时间线切换本是悬疑剧加分项,但《黄雀》硬生生玩成了“鬼打墙”。同一场抢劫戏从警察、反派、路人视角反复回放,凑时长的意图比佛爷的假金表还晃眼。当一部剧需要观众拿着Excel表格理时间轴时,它的叙事已经彻底失控。
最令人不适的,是剧集对犯罪的美化倾向。编剧给每个反派都发了“悲惨世界体验卡”,却对受害者只字不提。阿兰偷空老人存折后,镜头忙着拍她对着晚霞流泪;财神撬开保险柜时,BGM竟带着悲壮史诗感。这种“加害者比受害者更值得同情”的扭曲价值观,宛如给小偷递刀、给强盗打灯。当犯罪动机被浪漫化,法律与正义就成了剧本里的摆设。
对比经典刑侦剧《重案六组》,同样是刻画犯罪分子,《黄雀》输得彻底。前者用冷峻笔触揭露犯罪代价,后者却用柔光滤镜给反派写“伤痛文学”。当年轻观众在弹幕刷着“阿兰好飒”“财神好惨”,这部剧早已背离了刑侦题材的初心。
《黄雀》的崩盘,给行业敲响警钟:靠热搜词条堆砌的热度终会反噬,用“多线叙事”“人性深度”当遮羞布的创作注定翻车。观众或许会被预告片的光影骗进剧场,但绝不会为逻辑崩坏、三观歪斜的故事买单。下一季的坑已经挖好,但扪心自问:我们真的需要一群“身世凄惨”的盗贼继续在荧幕上撒狗血吗?与其硬凑续集,不如把片酬打给反扒民警当顾问费——真实案件的惊心动魄,可比编剧的脑洞精彩多了。